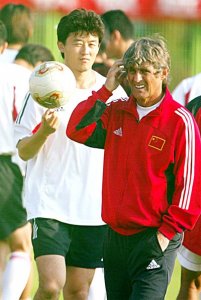农村消失的手艺人石匠
农村消失的手艺人之六石匠
农村消失的手艺人之六——石匠
文:李宝良。
图:网络。
石匠,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可能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可是,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手艺。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石器开始的。至少在两个方面为人类进化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让人不断思索与琢磨,使大脑更加发达;二是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出现的石斧,石刀、石锄、箭簇等,让人渔猎时与野兽有一个安全距离,收获大而且多,受伤小而且少;可以从山洞里搬到平原,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繁衍出更多的人口,成为自然界生存最成功的物种。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多少轮回,制石工艺仍然没有脱离最初的路数:打砸敲击制型,铲磨刻刮制面。无论是走乡串户的石匠,还是錾碑刻字的石匠,工艺无出其右。工艺无两工具也很简单,简单得让木匠嫉妒恨,让铁匠咬牙根。石匠的工具只有两样:铁锤和錾子,如果铁锤的一头夹有钢片,那也是琢磨平面的器具,丝毫不妨碍石匠使用铁锤击打錾子。加个钢片就是另一种工具,未免太魔幻了,木匠、铁匠看看自己为数众多的工具,几乎一个工序就需要一种工具,繁杂厚重挪个地方需要搬一大堆东西。石匠简单干练的工具,轻快得拿起就走背起就跑,怎不能让人羡慕。这只是石匠的一个方面,岂不知石匠也有令人心酸的一面。石匠的活计就是不断地挥舞铁锤击打钢钎錾刻,不断地挥舞铁锤...........无休止!另一个工艺是平整乃至修出平面,也是先用铁锤另一头夹着的钢片,像小鸡啄米似的点啄石头面,大体平整后再磨、磨、磨、磨.........无休止地磨,直至磨出平面光亮照人,再篆刻文字或者錾刻词句语录。

石头,从第一个掷出的石块击中兔子,到用尖锐面切割兽皮,打制石器就翻开了人类进步的华章。这篇华章发生在二三百万年以前,第一代石匠就此诞生。他们是人类的工匠,其创造意义不亚于一次工业革命。他们一手拿石块做锤,一手拿另一块石头做料,琢磨能砸打出什么东西。如上图,就是人类打制的手握斧。
现代的石匠右手握的是铁锤,左手执的是钢钎,打制的依然是坚固的石料。加工的对像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的脑容量,是思维。在千锤万锤的重复敲击中,石料变身为工具。

上图是新石器时期的石斧,上百万年的进步才有了磨制石器。形制规整刃部锋利,固定在另一种工具上成为一种组合武器或者工具,效率大大提高。加长了胳膊有了挥舞的余地,这应该是机器的范例,开创人力、工具效率叠加的先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石匠的工具进步是冶铁业发展,钢材造就钢錾,凿削有了利器,十分坚硬而且耐久的石头又变身为建筑材料,砌垒出了宫殿、桥梁、金字塔、城堡。再到装饰物品如华表、石狮、栓马桩,再到记载人、事、物文字的载体,就是各种石碑,例如西安的碑林。留住形象的是石刻,诸如:甘肃敦煌的佛像洞窟,四川乐山大佛石刻。汉武帝陵前的马踏匈奴石刻,乾陵前伫立的六十一尊王宾圆雕石像,陕西礼泉县昭陵北司马门外的扬蹄飞鬃六骏石刻像。阿富汗的巴比杨大佛石刻。还有西方国家及埃及众多的方尖碑。更令人叫绝的是秘鲁马丘比丘玛雅文明的石头城,山巅之上的城堡,石头砌得严丝合缝不留余地。这样的石匠工艺称得上登峰造极。

石匠,从远古走来,在锤击“当当”声中增加了人类的脑容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无数的“高大上”建筑。渭北高原上的石匠锤声“叮当”,无缘壮丽辉煌却满含民间烟火色,为农耕生活奏出和谐的乐章。

小麦是从两河流域传来的物种,在以“粒食”为主的食谱中还被视为是粗人、农人的食物,王公贵族不屑于食用的东西。说这个话的人很有分量,他是在隋朝唐朝都做过大官的人物颜师古,有原文“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为证。他作为唐高祖李渊的高官中书舍人,起草敕书王命,后又奉唐高宗之命考定“五经”。以考证严谨闻名于世,自然没有虚妄之词。那么,麦子比起小米、黄米、豆类来无疑是高大上的存在,为什么身价如此之低?试想,麦粒蒸出来或者水煮成饭,有麦皮阻隔一个个麦粒清清爽爽不粘不连,却难以下咽,咀嚼起来食之无味。古文献上记载“军中无粮,至有麦屑十斗”。这“麦屑”就是压破的麦粒,士兵们不爱吃算不上食物。甚至我们都有体会,夏季偶然喝一次麦仁饭,尽管脱去了麦皮有点糊味仍不可口。
麦子,如今是大多数人的可口食物,当初在东方大国的待遇犹如珍珠弃土,黄金匿尘。看看当今的尼泊尔山民,黑非洲落后部落,用石棒木棍在石板上碾压粮食,这就和先秦以前的人一样,把原粮简单碾压食用。能好吃吗?不仅不好吃还连累麦子在一千多年里不能变成美味。
石破天惊,一个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它就是石磨。石匠的功劳,一点也不用谦虚推让,石磨是谁发明的已不可考证,它出现的最早时间是东汉年间。麦粒在两片石头之间磨擦,褪去了皮露出了白色的内核,再磨碎成细粉,面粉出现了。有了面粉就有了食物变化的基础,面粉加水熟化后就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糊精,口感细腻,麦芽糖的成分让人在口腔里就感觉到了甜味,而甜味是五味之首,有此美味能不能让万千大众垂涎之,攫取之?麦子换上了美丽新装,登上了五谷之首,从“农夫野人之食”,成了达官贵人口中食胃中物,农夫野人竟然没有了吃的资格,天道轮回何其遽也。
后来面粉蒸、煮、煎、炸出各种美食。蒸类:馒头、花卷、包子。煮类:面条、水饺。煎类:煎饼、点心。炸类:油条、油饼、麻花。这些锦上添花的厨艺,演绎出琳琅满目的食物品种,谱写出社会发展的瑰丽华章。出发点就是石磨,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工具。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吃不饱吃不好,说其他的都是浮云。再说战争,打仗就是打后勤。简单易带的面饼是士兵征战的最佳干粮。比起需要蒸煮的小米来优点多多。极端一点说,刀剑的锋利比不过石磨的磨合。
石磨有书记载的时间是东汉年间出现,开始是两片石片磨合,中间有些许小坑,用以磨擦麦粒。经过长时间的改良改进,最后定型于圆形石磨,上下两片,一片动另一片不动中心一短轴定位,两片石盘磨擦面刻有特殊的沟槽。这些沟槽的设计颇有深意可谓机关巧妙,并且衍生出了一个独特的石匠工艺——锻磨。

石磨的沟槽以磨轴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有等分的六扇面、八扇面、十二扇面。圆周越大等分数越多,直达中心的棱条就是等分线,并且以逆时针分布。沿等分棱条再逆时针等分小扇面,这些等分的小齿条间距根据研磨粮食的种类决定齿宽,但是,磨齿面都向心倾斜,越是边沿石齿越浅,越是靠中心石齿越深,这样的结构利于粮食从粗到细研磨。大些的石磨上片,在中心大约十五厘米圆心,錾出一个深达二三厘米的凹陷,名称叫“磨膛”,储存由磨眼里下来的粮食,避免石磨上下两片之间没有粮食研磨,出现“干磨”加快磨齿损坏。上磨膛还会凿出导流槽,石磨研磨粮食的过程,就是转动的磨齿把粮食按原粮→粗粒→次粗粒→细粒→磨沿依次推出,上下磨齿挤压磨檫,棱线推刮、切割。一个小扇面一个加工区域这样的流程循环往复,经过细目箩筛分离出面粉和需要继续研磨的麸皮。动力来自于人力或者其他畜力、水力。磨盘的转动方向是逆时针,由于上下磨盘都是逆时针凿齿,不会出现磨齿啮合,反转也能转动,我小时候出于好奇心,试着反推石磨,转几圈过后粮食从石磨的磨眼里翻上来,石磨也发出干磨石头的声音,被大人立即制止,知道这会磨坏磨齿,要花钱请石匠来“锻磨”。
“锻磨”并不是一个石匠的专门称谓,只是一个石匠工艺。因为,锻磨是石磨的修理过程,包含錾刻、琢磨、钎孔、溜圆等工艺。全是石匠的主要作业,不是另立的门户,没有独特的工具和工艺。只是因为锻磨的石匠和小麦产区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经常出现在千家万户里而已,把它看成一个独特的行当就不足为奇。
石匠的工具里比较有特点的是钢錾。粗细大小型制不一,材料都是中碳钢,常见的是∅18——∅22螺纹钢,高碳钢被打制成刻字用的刀具,篆刻用的刀具就是白钢制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石匠和铁匠没有门户之见,更多的是合作,相敬如宾也不为过。石匠的工具都由铁匠打制而成,但是,钢錾、铁锤锻打出样式,淬火却由石匠自己来操作。就是说最能显示铁匠手艺的时候,铁匠礼让石匠来完成。在其它手艺人的行当里完全不可能。这实际上有充分的实用依据,铁匠打制的刀具刃部淬火体现了铁匠的手艺,切割肉类砍劈木材,都是以硬就软、以硬就弱,自然越锋利越好,韧性的要求在其次。石匠用的钢錾却是用在石头上的,两硬相遇两强相博是谁给谁塑形修身?,是谁给谁磨砺折颈?,其微妙其神秘妙乎其哉神乎其神。点化之功在乎三个匠工某日碰头问候时就说出了个究竟:有一日木匠铁匠石匠不期而遇,三个人说了三句话。木匠问候铁匠和石匠:二位师兄从哪里来?石匠说:我从天上来。隐喻历史久远艺自天成。铁匠说:我从空中来。隐喻无中生有是铁,陨石雷火来自空中。木匠说:自然我从地上来,隐喻木生于土。就请二位师兄先行。石匠礼让铁匠先行,铁匠正色道:你我本出同源,但是你以硬对硬又刚又韧,我要用火烧软了才能打铁。另外世上留存最久的东西都是石匠的遗存,你应先行。
石匠大多都会给钢錾淬火,他们淬火用的材料也跟铁匠淬火的材料不一样,他们用稀泥巴淬火意在缓慢回火增加钢錾的韧性。钢錾头高强度的部分尺寸很短,大概在几毫米之间。个别高手会给钢錾头磨生(渗碳),錾刻用的利刃还会使用密不示人的牛皮骨角回火(渗氮)工艺。仔细看石匠用的钢錾头部呈纺锤型,俗称扁豆棱,一面稍宽是刃部,一面稍窄是棱线,并非很尖细或者很钝。熟练的石匠很少几锤打断钢錾头,打歪钢錾头。
石匠的铁锤跟普通的榔头不一样,一般分量大,大约是两个普通榔头的重量。型制也不一样,锤体呈长方体,锤把安在偏心位置,铁锤一端稍长是击打钢錾的锤面,方形锤面是贴钢工艺打制。一端稍短,中开一个裂隙用于夹持一枚钢片。琢磨磨齿就如下图操作。

石匠工作就是千锤万击的劳动,每一个平面,每一个棱线都是钢錾击碎石头的过程,右手执锤左手执錾就是固定的模式。全部是利用手腕部的力量,没有机会和方式来利用躯干或者腿部的力量,甚至连利用大臂力量的机会都很少。稳定的身体重心是执錾挥锤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的石匠操作都是看见他们团坐在石头旁边,挥锤击打手中的钢錾,锤声叮当碎石飞溅。岂不知左手执钢錾颇有技术要求。左手执钢錾时,侧握钢錾与石头加工面呈45度夹角,在锤击力量到达錾刻点的瞬间挑起錾尖,击飞碎石。这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也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不动錾头连续两击之后的结果,就是石粉飞起钻出了一个小洞,要挨师傅的骂了。石匠的误操作代价很大,一个平面的修正意味着另一轮千锤万击,不像木匠的几斧子砍削,铁匠再费一炉炭火,容易吗?长时间的练习,石匠右手的铁锤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不管钢錾后尾如何上下左右移动,石匠的眼睛只看钢錾的尖头和石头的接触处,雨点般的锤击落点就在钢錾的尾端,不偏不离,力度恰好准确无误。

锻磨的石匠农村人经常看到,实际上是个很精细的工作。集合了石匠錾刻,琢磨、修面、裁体、分割等工艺。人力推动的手推磨,磨盘小一般作为磨豆腐磨小米杂粮的用具,大多用青石制作,上下磨盘錾刻全磨盘磨齿,没有磨膛,齿条小而密,町线(用同音字代替)直达磨心,推起来省力轻快,力气小的妇女老人都能推动。常看到老人站在小石磨几米开外,双手握一根短横木,推动长杆连接的石磨转动,黄豆的浆汁从磨缝里流出来,这就是磨豆浆。
磨小麦的石磨直径在90厘米左右,用牛或者毛驴拉动,牲口用绳索套在木杆上,木杆的前头一根缰绳牵着笼头,训练好的牲口蒙着双眼,歪着头拉紧缰绳就保持了和石磨的距离,绕着磨道转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人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在自家的石磨上磨面,前拉后推一家子人忙。有月亮的晚上还好受些,碰上黑沉沉的夜晚,我常在推磨的时候转得昏天黑地不辨东西,晕晕乎乎似睡非睡,搭在磨棍上的手那里还能使上力气,只是跟着大人的脚步机械地移动,隆隆的石磨声最能催眠。石磨是最让人厌烦的东西,可是,晚上不去推磨就吃不上白面,看着石磨真是又爱又恨。刚刚锻好的石磨一个多小时就能磨好一斗麦子,常常让人大喜过往,最后几圈推着石磨转圈快跑,对石匠的锻磨手艺感慨不已:是石匠解放了我们不在深夜劳动。
用水力带动的水磨石盘直径在一米五左右,磨齿长而且多,磨面效率很高。这些大小石磨是农村磨面的唯一工具,打制石磨修理石磨的锻磨石匠就很吃香。周原附近的王石万沟出产石磨,近百里远近闻名。这些大型石磨的石材是花岗岩,晶粒为中粗粒和细粒,其中的主要结构物是石英,石英是自然界次硬的物质,虽然錾刻不易但是坚硬耐磨,磨削粮食自然是小试身手无坚不摧。最重要的是花岗岩浑然一体,没有水纹裂隙及层状结构,可以凿制大型磨盘。北山山脉的瓦罐岭附近一处石头山名叫方山,出产一种石灰石,碳酸钙成分较多,质地细腻,颜色墨黑的一种石头被称之墨玉石,是凿制石碑的上好石材。这种石头颜色丰富,有青白色、白色、淡黄色,被北山人统称之青石,质地较脆有纹理有裂隙,红色的裂隙是氧化铁附着,略透光的石质看起来非常明显,不能凿制大的石磨,但是非常适合凿制磨豆腐的小石磨,细腻的石头磨面光滑。泡好的黄豆质地软糯,青石磨齿也没有花岗岩石磨磨齿尖锐粗砺,没有颗粒状的石粉磨出,做出的豆腐口感很好,小石磨都是青石磨。
农村人的生产生活都有石匠的手笔,在我们村子里小到石锤、石臼、石盆,大到石磨、碌碡、石碾,路边的路碑、祖坟里的纪念碑,更大的是生产队饲养室里的石槽,长约五六米宽约一米深约六七十厘米,像一段中空圆柱体被从中间一劈两开,放在地上供牲口吃草料或者饮水。这些巨大的石槽是我看见的最大人工石质构件,更为石槽外面莲花图案,奔鹿飞鸟草叶藤蔓图案惊奇,这些图案都是浮雕,手摸触及凹凸有致。石槽上没有纪年铭文,不知是那个年代那个石匠凿制。就是当初的大富之家“泰和丰”的后人,胡须斑白的老地主也说不出个究竟,只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石槽的内壁光滑细致跟本看不出錾凿锤击的痕迹,石槽的边沿还被牲口的皮毛缰绳磨檫出绺绺痕迹,可见石槽的年代久远。它是怎样凿制的是我心中一个迷。这个谜的起始点还在看到生产队的石槽之前,我家老院子里有一个半截石槽,倒扣在院墙边,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游戏时,这是我们的一个藏身之处。从石槽的残破处判断,这是一个储水的石槽,不像生产队石槽那么大,方形内径大约一点三四米见方,壁厚约八厘米,内壁光滑外壁浑圆,石质却是青石。十多年后,父亲给家里凿制猪食槽时,我才看出了个大概究竟,算是解开了石匠凿制水槽这个迷。
生产队的时候农村家家养猪,是唯一的副业,也是为自留地积攒农家肥的唯一途径,既是唯一事业就特别上心,可是没有精饲料,惹得二师兄好不高兴,想方设法闹别扭,特别能干的猪鼻子能掀能挪还能挖,在满是谷糠的猪食盆里搜寻粮食,无法满足意愿时就咕嘟咕嘟吹泡泡,恼怒之余轻轻撅起鼻子,就把铁制或者木质的猪食盆掀翻在地,再踩成一地烂泥巴。有石匠手艺的父亲没有因为这个畜生生气,他有了主意,在堆满石头的深沟里找来一块大青石,他要凿一个猪食槽,优选石料是麻杂石(花岗岩),可是花岗岩石料在几十里之外,为一个猪食槽费心把力跑几十里实在不划算,看这块青石料没有裂隙水纹,尺寸还差不多就凑合着用,青石料性质太脆成功的把握并不大。
石匠的选料谋划和其他匠工一样,远观近看四面端详,只是因为石头重量大不易翻动,估摸起来费些心思。在动手之前石匠父亲用上了墨斗尺子,还用垂线和方尺在石头上画出了轮廓线,想先凿出两个平面,看看石头的质地再作进一步的谋划。然后在上工下工前后拿着钢錾铁锤叮叮当当凿起来。
錾刻轮廓是处理毛料,锤击的力度很大,凿起的石渣也是大块的石片,用的钢錾也很特别。

这个钢錾头很短只有十二三厘米长,用铁皮做楔夹在粗铁棒一端的圆孔里,这个粗铁棒呈纺锤型两端粗中间细,另一端装小段粗木顶端套有铁环,作用是铁锤击打木柄时木头不易劈散。这个工具专用于开凿荒料,名叫:钵条(关中方言意指捻麻线绳的吊槌,用其音。),有重量有刚度。其原理是锤击的动量传递到钢錾的尖端开凿石头,长细比很大的螺纹钢钢錾传递动量时,有一部分动量,被钢錾的细腰身部位发生的弯曲弹跳等变型消耗掉了。在大力量锤击时动量损失特别大。钵条的使用让锤击的动量完全传递到錾尖,避免了动量损耗提高了功效。缺点是左手腕负担大很容易疲劳,所以只在开凿荒料时才用。
三天后,一个基本规整的石料打凿出来了。轻凿轻打出的是断面为梯形的六面体。打出的白色线条笔直流畅,各个立面平整。关键的一步将要开始,在这个六面体上凿出食槽。先优选出一个可以开口的平面,用方尺墨斗画出净料尺寸线,要开凿盛猪食的深槽是最后的工序,让人想不到的是,先要在靠近槽底的部位开凿出一个污水清扫孔。父亲告诉我这么做的原因:凿好的猪食槽边厚仅有三厘米,最后开凿清扫孔容易打裂石壁,在一个厚实的石体上凿孔就保险得多。为了避免最后几凿打坏石槽功亏一篑,开凿石槽依然需小心谨慎。果然,开凿石槽内部花了几天的功夫,用的工具身材纤细,铁锤击打的力度分外轻巧,每次凿起的石渣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清脆的叮当声在小院里起起落落,经久不息。终于一个青石料的猪食槽凿制成功。猪食槽的内底面做了光面处理,是用一把废旧的砍柴斧头轻轻錾击,去掉凸起,再削磨一番,最后还用破布压着石英砂来回摩擦增加光洁度。

其实,生产队大石槽和我家猪食槽的凿制工艺大同小异,要说青石的猪食槽凿制难度还大一些,青石材质发脆,碎裂的几率要大于花岗岩。青石质地细腻比花岗岩软,磨削容易却是錾刻石碑的材料。方山的半山腰就有前人开采石碑料的矿场,听人说还是质量上乘的青墨料,和乔山东麓富平县的碑料有得一比。
如果说锻磨的石匠连接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錾刻石碑的石匠就是一个文化二传手,他们的工具精湛锋利轻巧纤细,文化素养也高出一个等级。是高级人士,其中的佼佼者还是艺术工作者。毕竟文章冠天下只炫耀于当世,书法飘逸绝昆仑者也称奇于足下,想要流传千古贻芳百年,别无他法,只能寄托于石碑。留存要久刻制则难,在石碑上刻字做画只有艰辛没有潇洒,锤声当当刀声戚戚灰尘扑面眼看手摩,何止一个匠心了得。粗通文墨是最基本的知识,书法大家的神韵笔法需要刻碑石匠的心领神会,才能细致入微地体现出来,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传神入画于时无。非如此,“疯张”书法的飘逸,其仙风道骨何以张扬于后世,碑帖如何洛阳纸贵。“楷书极则”之碑《醴泉铭碑》,被后世千年临摹拓帖,石碑表面都摩挲得凹凸不平,有倾慕者看到石碑刻文大呼三生有幸涕泪交流。欧阳询固然值得称颂,刻碑的石匠何尝又能让人忘怀,没有石匠的艺术再现,欧阳询的楷书就不可能留存千古。
石匠,连接着生活创造着艺术,从远古走来一路辉煌。
农村的石匠和所有的农村手艺人一样,在现代的社会中走向了没落。石磨这个最基本的磨面工具被抛弃了,石碾盘连同石磙被推到了墙角土坎下,多少代人手指衣服磨挲得光滑的石碾盘底座,也被人拉去烧了石灰,因为它是上好的青石,烧出的石灰质量好。钢制的磨辊代替了石磨的磨削挤压,偏心轮筛代替了手动铜丝罗,速度快了十几倍。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甚至都没有给石匠们谢幕的机会。绿色环保的水磨也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消失在山林绿野之间。没有了需求的石匠就无人问津,寒来暑往日月更替,石匠们白发覆盖了头颅皱纹布满了面额,腰弯了腿瘸了,手挥不动铁锤,眼看不清纹路,老了。土地接纳了他们的躯体和他们的手艺连同工具。石匠成了历史。
2022.02.09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