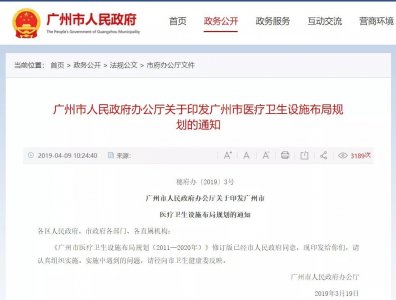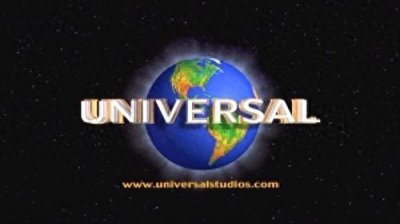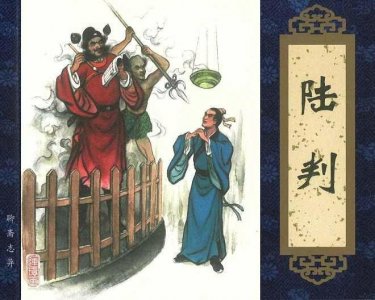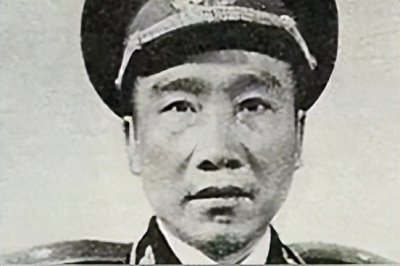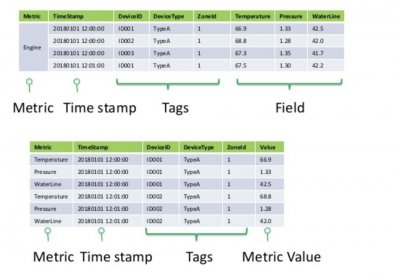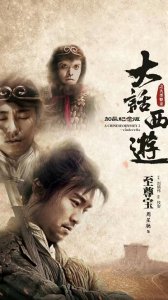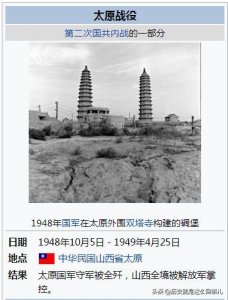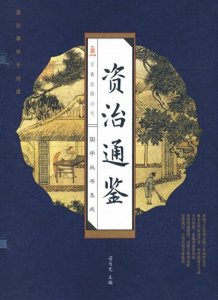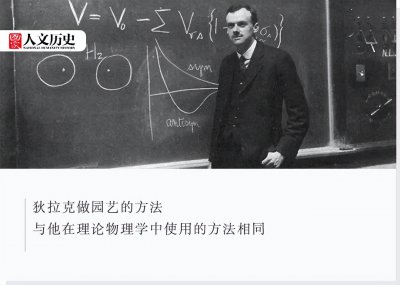红军长征的宿营(上)
红军长征的宿营(上)
安营扎寨本指军队搭帐篷、修栅栏住下(现指军队或某团队的临时住宿),分为舍营(利用居民房舍住宿)、露营(在房舍外露宿或用帐篷住宿),或两者的结合,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军队编成来确定宿营地。它是军队最原始的需求之一,能使人得到休整以便继续行军和战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既要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又要跋山涉水的艰辛条件下,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宿营条件无保障,红军长征却硬是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难关而胜利了。
一、长征宿营
红军长征常寝食不定、昼夜兼程,能停下来休息已算是好的,遑论宿营条件如何了。为身体健康着想,中革军委要求红军指战员尽量不要在阴冷天气和雨天露宿于野外(能睡在牛圈、猪圈堆草的楼上也好)。1934年12月19日18时半,《朱德致各军团纵队二十日行动部署电》要求:“各兵团均应到有家屋处宿营,……”据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朱总司令、毛政治委员、周副主席……指示:‘为着避免部队露营疲劳,为着容易找给养,还是再前进几里路找房宿营为好,该地房子是准备留给干部团的。’”
1.分散宿营
红军长征后,因身居白区、分兵作战和长期处于运动战状态,已不具备全军集中建营房的条件。但红军总部仍十分重视宿营问题,由各军团指导宿营,各基层部队因地制宜自建设营队而分散宿营。作为先于大部队行动的设营队,一定要随机应变,侦察能力强,能观察地形是否适宜安营,确定住地是否易守难攻,饮水可有保障,等等。据军委干部团学员曾万标的《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载:“这幢小洋楼是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有20多个房间,楼房四周是一片开阔地,30米以内没有障碍,非常便于警卫。”军委纵队第一梯队20多人的设营队,曾在离云南曲靖不远的一个大镇智取过当地反动民团。黎平整编后,张云逸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其任务是为纵队探路设营、派出分队了解社情、侦察敌情等。据红军总部一局参谋吕黎平的《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载:“……作为军委纵队的先遣司令,率领有关部局的部分人员,负责先行打前站,侦察地形和敌情,筹措后续部队的食宿等工作。”据先遣队司令部电台负责人袁光回忆:“先遣队司令部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为中央纵队开路设营,经常比大队人马提前一两天行动。”
尽管戎马倥偬,但对长征设营队的管理却从不放松。1935年9月27日,《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关于目前群众工作应注意之点》要求:“为纠正设营队忽视居民工作的现象,应立即采取:(一)设营队内设政治委员,一切政治的、对群众的工作问题,要由他负完全责任。(二)设营队到达宿营地时,必须召集群众谈话开会,解释清楚我们为何向他们借房子住,然后进行设营工作。(三)设营队须有严格的纪律,不得有乱翻东西、乱搬锅子、门板等不良现象。”
2.借宿民房
长征中,红军依然借住民房。因相信革命宣传,沿途群众热情欢迎守纪的红军,有人甚至主动要求红军到自家住,保证了红军每到一地都能顺利借住。长征“半条被子”的故事,讲3名女红军借宿于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她留下了。1935年1月5日,林彪、聂荣臻签署《红军第一军团对执行城市政策之规定》,要求:“入城部队当其战斗任务完毕后,除派出必需(如需要派出时)警戒外,余应立即开出城外,集结在城郊宿营。……在城内驻宿的部队,一律不许驻商店,并应保持自己宿营地的特殊。”
虽有沿途群众支持,但因行军队伍距离拉得长,后队很难了解前队的情况,如何找住处便着实成了长征红军的头疼问题。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晚上找宿处:教导营因房子不够,只有继续前进去找房子。沿着广阔的山脊,两面都是壁陡的石崖,不能下去,又不见有村庄。走了三十里,找到一个破旧的房子,又被军委直属部队先宿了营,……于是我们又继续前进。又走了大概八里路,找着了几间小小房子,分散了休息,已是半夜一点钟了。”
不扰民的红军即便是住进百姓家,主人在家时,也只住在堂屋或二楼,绝不入内室睡;主人不在家时,就在走廊等处铺禾草、睡席打地铺。但不管怎样,在离开时一定会扫地干净、捆好稻草、装上门板。为鼓励守纪,红军还开展宿营模范评比活动。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刊文《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指出:要“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据警卫员张华回忆,彭德怀曾在贵州遵义懒板凳教育他要恪守军纪:“这里是新区,老百姓还很不了解我们红军的政策,他们还把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看待,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老百姓的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是怎么借来的,就要怎么归还,别看这是一块门板,它会直接影响到红军的声誉。”
3.住洋楼豪宅
为避免露宿疲劳和便于补充给养,红军有计划地将城镇中已闻风而逃的土豪、官员的房子用来住宿,所以红军也偶尔住过军阀的洋楼、土劣的豪宅。据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934年“12月21日……按军团部通知,我们今天在剑河休息一天。……供给部住在其左侧的一家地主院里,监护连、兵站,运输队亦都住在附近土豪家里。”红军总司令部在贵州黎平城、遵义城期间,驻扎在富户胡家宅院、柏师长公馆里。据曾万标的《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载:“随后,中央领导也陆续来到遵义城内,住进了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小洋楼里。”博古、李德在遵义城期间,住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七师副师长侯之圭(侯小白)的私宅;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城期间,住在川南边防军旅长易少荃的官邸。据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桐梓城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一座座,相当讲究,据说贵州省的许多军阀、官僚、富商发了财都在这里建一幢别墅,……待我们红军进城时,这些达官贵人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一座座的空楼了,这正好为我们腾出了营地。……我们命令,每排分住一座洋楼。”
每当指战员占得敌军营房后,首先让给伤病员、女红军、红小鬼等更需要较好住宿条件的人。据红军卫校教育长李治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载:“当我们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广大洋房内,收容了娄山关(贵州通重庆的一个险要的关口)战役的重伤员(干部),……”
4.驻公共场所
宗祠、官署、会馆、庙宇、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常为红军宿营地。据《康克清回忆录》载:“宿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找当地的祠堂住。”毛泽东在瓮安猴场期间,住在下司傅氏宗祠。据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2月21日……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均住在县衙内,……”据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的《从闽西到京西》载:“……随军团司令部行军西进到贵州黎平县。军团司令部在县衙内休息了一天。”据曾万标的《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载:“那是1935年1月11日拂晓,中央干部团一行一千余人,分批进入遵义,进城后住在一所中学里。”博古、李德等人在黎平城驻扎期间,住在福音堂里。红军进入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机关驻扎在老城的天主教堂内。扎西会议在云南威信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两河口会议在四川懋功的一个关帝庙里召开,榜罗会议在甘肃通渭榜罗小学召开。
5.野外露营
“天当被、地当床”,红军常在荒野宿营,盖破棉絮、棕树叶;或在树下、草堆旁、田间地头和衣而睡,把油布铺地或罩顶已属奢侈。1935年8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应采取一切方法(搭棚子、帐幕)来组织露营。”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连外面的草坪里树下都挤满着人,……”据随红六军团长征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载:“士兵……都是头枕包裹,就地而卧,我们周围的泥地上都躺满了,连我们下脚的地方也没有。”据[美]布热津斯基的《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载:“为了取得农民的尊敬和支持,红军战士曾奉命借用这些门板在户外露宿,不征用民房。”

图注:《遵义会议》
红军不擅入民房,一是守纪,二因无房。长征沿途,反动派命人藏粮、烧房,导致红军“要吃没粮、要住没房”。广西军阀派人烧房的目的之一便是想让红军难安宁,不敢住进村庄。虎落平阳,分外凄凉。为加强驻地的防火工作,红军规定宿营地必须要有盛水的木桶。1972年,周恩来回忆:“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住房。”据陆定一的《长征大事记》载:(12月7日)“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1935年5月,红军借道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大凉山彝族区而去渡大渡河。其间,地方工作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强调红军只是路过而绝不在彝人村寨住。
6.奇葩站睡
因条件有限,红军有种奇葩休息法——拴起站着睡,即把自己捆在树桩或板壁上。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看护长王太钧忆及在贵州黎平城的情形:因人满为患,场所、铺盖奇缺,王太钧与另一人站着将背贴于花格窗两边的板壁上,然后用一根红布带从窗格中间穿过,下垂的两头则分别系在他俩腰上。这既可以防止人坐或倒卧于阴冷的地上受潮着凉,又可使人能勉强得到休憩。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也有类似回忆:“我们累极了,我们把自己拴在树干上、枪杆上,彼此背靠背,……我们站着睡、走着睡,满脑子想的净是睡,但实际上睡不着。”
7.夜宿草地
长征前后期的宿营艰难,不可同日而语。经过死神统治的草地时,红军常被泥泞渍水所浸,或铺枯草等露宿,或就地而卧,或背靠背坐着取暖、打盹,或掘土洞搭草窝避风。因饥饿、长途征战致体力透支,以及健康人都难以抵挡的、伴随着寒夜而来的雨水和冰雹摧残,加上缺医少药,使伤病员大增,每天掉队的不少,牺牲者有之。据红五师宣传科科长谢扶民的《草地行军六天缩影》载:“今天到下午时正下着毛毛雨,今晚我们就在树下搭起帐篷和架起睡铺,帐篷大部分是以单被,小部是以油布搭成的,……我们的炊事员同志到睡觉的时候,上面是搭起了帐篷,下面是扁担架起的床铺。这种床铺是两头放着钢锅,中间横架一条扁担。睡下去是两脚落地,面朝星星。”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到达宿营地时,各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齐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
二、宿营后的工作
到宿营地后,除有人因鞍马劳顿倒头酣睡外,更多的人则在做下列重要事情。
1.组织警戒
派出警戒力量放哨(排哨、班哨、步哨、游动哨等),及时发现敌军和敌特侦察、突然袭击、破坏,掩护各部休整、机动展开等。长征中,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先后兼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军委纵队驻地卫戍司令,其主要任务是率部调查敌情、扫除敌探,保卫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宿营安全。遵义会议期间,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便率部负责会址外围的安保任务。
2.研判备战
一是每天到达宿营地,参谋总不能闲,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更要查地图、看电报、听汇报等,了解敌情、我情等,研究下步军事部署和行动。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除听到无线电充电机的声音不间断的叫着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大家很疲倦的休息去了。在一小房子内找着了朱总司令、毛政治委员、周副主席,大概是在布置明日的行动大计。”据警卫员顾玉平回忆:周恩来一到宿营地,便看电报,写东西,找人研究路怎么个走法,……。二是各级首长将下级报来的资料统计报告给上级首长,与下级干部谈教育等及研究发现的问题,军事主官、政治主官各司其职;深入排、班,检查督促指战员休息,加强查铺查哨;督促指战员擦拭武器,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准备器材。
3.开会发令
长征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中央负责人会议、各级军事会议(诸葛亮会)等,常在宿营地召开。虽在行军甚至战斗过程中,有可能就某些紧急问题开“飞行会议”来碰头研究,但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往往是很难议决的。到宿营地后,更多的相关领导可在较宽裕的时间里聚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充分而激烈地讨论,统一意见后再作决定,并发布命令。这也是湘江战役后(此前主要是为防敌机侦炸而夜行晓宿),重要会议一般情形都是在夜间的宿营地召开的原因。
4.宣传群众
(1)革命宣传。红军未到,群众已上山躲“匪”。兵荒马乱,盗匪乱窜。政治部门要求红军向群众做好宣传,以争取理解和支持。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刊文《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指出:“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1934年12月5日,《红星》报刊文指出:“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标语内容以“打土豪分田地”“挖富济贫”等为主,它能最迅速、最大程度地唤醒和吸引群众。
无论是在战斗、行军、宿营时,还是身居城镇或行进途中,红军宣传员利用喊话、贴标语、插竹(木)片、发传单、唱歌、演戏、画漫画及“漫画式标语”等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在砖墙、板壁等上面用粉笔、颜料、黑锅灰书写,扩大党和红军影响,为克服艰难险阻作贡献。当年,有首顺口溜说出了宣传员的辛劳:“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脚杆没得闲。”
(2)开群众会。易被反动宣传所蒙骗的善良百姓,也容易为红军所争取。红军曾经多次在长征沿途的一些人口集中地召集群众开会(人多开大会、人少搞座谈),以当众惩恶扬善。宣传红军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批斗地主,分发土劣浮财,驳斥反动派对红军的不实污蔑,动员劳苦群众参加红军,号召民众各安生业而勿自造恐慌,等等。在《红星》报长征专号第7期第2版中,《黎平城的群众大会》留下了宝贵记录:1934年12月18日,红军在黎平城荷花塘召集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1937年,朱德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我们还举行群众大会。文工团给老百姓演戏唱歌,政治工作人员则写标语、散传单。”(未完待续)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张中俞